专访|编剧王小枪:剧本创作就是马拉松,沉住气别疯跑
- 财经知识
- 2025-04-10 09:12:05
- 23
“编剧就像一个厨子,每个饭店都有鱼香肉丝和烤鸭,但我希望能端上一道别人没见过的菜。”
在编剧王小枪的创作哲学中,这种对“差异化表达”的执念贯穿始终。从《对手》中将中年危机嵌套进谍战叙事,到鲜少于荧幕上出现的聚焦基层干部日常工作的《县委大院》,再到最近《黄雀》以反扒民警与小偷群像为切口,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类型化的框架内寻找新的表达路径。
对最近播出的电视剧《黄雀》,王小枪表示,希望在刑侦剧题材的“拥挤赛道”中另辟蹊径。这部以千禧年前后的火车站为背景的反扒剧,通过正反两派的群像交织,展现了小偷、诈骗、传销等犯罪形式的众生相。

《黄雀》海报
为了让故事和人物更加真实可信,他深入公安局体验生活,与反扒民警一起工作抓小偷。还掏出了自己多年前的被骗经历,剧中出现的那个八十块的打火机,就是王小枪的“真·血泪教训”。
令人印象深刻的是,《黄雀》中对犯罪群体的刻画并非简单的脸谱化处理,也让观众在“敌我分明”的类型剧中看到了更多现实层次。王小枪认为,群像剧的魅力在于,所有的人物和人物关系,会在叙事中形成“蝴蝶效应”般的合力——每个角色的行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,这种复杂性正是现实生活的镜像。

《黄雀》人物关系图
谈到行业现状,王小枪有着清醒的认知:当主流题材被反复消费,观众的审美疲劳不可避免,而未来“全民爆款”也将逐渐让位于“用户定制”。但即使“长剧短剧化”的行业趋势不可避免,他也坚持不盲目追求节奏的加快。他认为,剧集的体量应由核心故事决定,而非外部环境的标签化要求。“《红楼梦》无法压缩成短剧,而《世说新语》也难以拉长。”
在一个被“长剧短剧化”“倍速观看”裹挟的时代,如何让观众慢下来、沉浸其中?在王小枪看来,答案或许藏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——那些被时代浪潮裹挟的边缘人物,那些复杂而真实的群像关系,那些在褶皱中折射出人性光辉的瞬间,都能成为打开新叙事的钥匙。而编剧的任务,就是找到那些尚未被讲述的故事。

2024年6月26日,第二十九届上海电视节,王小枪出席白玉兰奖评委见面会。
【对话】
抓小偷比我想象的要难
澎湃新闻:在看《黄雀》的时候,观众几乎都忘了,我们曾经历过一个小偷那么嚣张的年代,这是几乎被遗忘的历史。像这样的年代记忆,前期调研收集资料会存在困难吗?
王小枪:也还好,总体上来说,我们小偷现在确实数量少了很多,但还是有的。难度最高的在体验生活,我之前去沈阳市公安局的某刑警大队,跟着他们一位支队长,每天跟着一起出工,回来一起在食堂吃饭。民警怎么想,小偷怎么想,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这些,我们现在剧里呈现出来的,基本都是那段时间得来的。
比如说贼分好多不同的类型群体,他们流派之间也有鄙视链,有的是技术流,有的是团伙,有的是个体,有的是固定的,有的是流动的,有的讲究体面的,有的就完全不在乎,甚至从场景区分,有专门吃火车饭的,有专门偷公交,有专门偷商场,还有专门偷演唱会和体育比赛的,全是细分赛道。
澎湃新闻:这些流派里,他们的鄙视链是什么样的?
王小枪:简单来说,谁真的是技术高,他们就服谁。他们都比较鄙视那种半偷半抢的。比如说街上抢人耳环,没技术,这太笨了,还伤人。还有道德上,他们也有鄙视链,总体上他们不太瞧得起那种偷病人和病人家属钱的,还有去医院偷东西的,他们觉得这有报应,咱不帮人也别霍霍别人。

《黄雀》剧照
澎湃新闻:能否谈谈这个调研里的细节,你谈到过跟着民警一起,在公交地铁上一圈圈地绕,好像是个很漫长枯燥的过程?
王小枪:对,抓小偷比我想象的要难,我以为这出去一趟,还不抓他好几个?后来发现三天抓不到一个。
比如我跟着警察同志去公交地铁抓小偷,某条地铁线的某几站,上个月的报案率明显增高了,就说明这几站小偷活动多了,那他们就会把这几站作为重点,一趟趟地在这几站来回晃悠。
抓小偷这事儿,不像刑侦重案,还能有些现场线索之类的蛛丝马迹。我跟着民警,就是在地铁上周而复始地坐,同时一直观察着车上的人。民警经验很丰富的,一看哪个人比较像小偷,就一直跟着,跟到他动手的瞬间,上去抓到现行,人赃俱获。而且还得失主配合,他承认他丢东西,且愿意做笔录,这个事儿才成立。所以整个过程非常漫长而繁琐,而且成功率很低。
澎湃新闻:剧里火车站作为一个戏剧发生的场景,融合了千禧年最常见的各种犯罪形式,从小偷到诈骗到传销,展现得特别齐全。其中有你真实经历过的吗?
王小枪:很多都是调研中了解到的,当然也有一些我亲眼所见的。我当时也正在外地上学,经常需要坐火车往返。有一次,我一出火车站,看到广场上有很多小摊,有一个卖那种不锈钢打火机的,牌子上写着五元一个。我想这很便宜啊,可以买一个。然后我还怕上当,反复跟他确认:你这真的是五块钱吗?他说真的五块。
确认好几次,我才说买一个,他说你想好,充上气就不退了。诶,我一听这就含糊了,可能话里有话,但问来看去,也没啥问题,就还是买了。一充上气,他就要八十了。我说大哥,你说五块钱诶。他说是五块啊,然后一指牌子上,有个折起来你根本看不到的地方:立减五块,原价八十五。

《黄雀》剧照
像蜘蛛网一样编织人物群像
澎湃新闻:这个剧写作上最难的地方是群像塑造。它以火车站为一个场景,展开了正反两派的众多人物之间的斗争,又在斗争主线之外,做了大量周边支线事件和人物,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群像?在创作中,怎么去搭建这个框架的?
王小枪:我当时写《黄雀》的时候,刚刚写完《对手》。《对手》还是那种相对传统的戏剧结构,郭京飞和谭卓如何面对来自正邪双方——颜丙燕和宁理施加的压力,然后经历一个个单元事件。我不是特别想重复写类似的东西,再加上《黄雀》是我写的第一个原创公安题材,还是想有一些突破或者不一样的东西。
之前我还看到一篇评论吧,谈到为什么很多以盗贼为主角的故事好看,比如咱们中国古典文学里有那种燕子李三式的故事,以前港片里也爱做侠盗,包括外国电影也爱做神偷,故事里会有很多刺激冒险的东西是观众爱看的。
但《黄雀》,我不想写成神偷故事,也不能做得天马行空,所以就尽量从人物去想,让每个人物都有自己一套非常合理的逻辑,他的成长、家庭和其他人物的关系,尽可能让每个人物都是立体的,那这样就会花费很多精力和心血。加上这些贼分各种不同群体,到了剧本创作上来,确实会比以前写过的戏、人物都要更丰富和难写。

《黄雀》剧照
澎湃新闻:几乎剧中任意人物和其他人物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这个创作过程中,你是边画人物图边写作吗?
王小枪:这个戏就必须画人物图了,它就像盖楼房一样,需要非常详尽的图纸。因为它太错综复杂,所以图纸也必须画得丝丝入扣。
前期画这个图,确实比较费劲,我还是希望每个人物都有效出场,尽量人物之间、前尘往事与当下发生都能勾连、呼应上,比如黎小莲找到弟弟时,花姐正好在场,郭京飞和祖峰也曾擦肩而过,前面出现的受害人姜吉峰,后面发现他和郭京飞、方慧是一组三角关系。这次的人物关系像蜘蛛网,每一个线头跟线头互相搭着,最后都是闭环。

秦岚 饰 黎小莲

郭柯宇 饰 花姐
澎湃新闻:所有的人物对故事要形成蝴蝶效应般的“合力”,你创作中是不是人物小传写得很长?
王小枪:对,而且实际上是我一直是分集思维,我会把很多东西想得特别细,才敢动笔,所以我基本上每次都不写大纲,我就直接写分集了。
编剧和导演,像“包办婚姻”
澎湃新闻:剧本创作难度大,对合作者也会门槛更高,需要合作者能看懂剧本的细枝末节。能不能也聊聊跟导演、演员的合作?
王小枪:说实话,编剧和导演的关系,有点像过去的包办婚姻,当然你也能打听一下对方怎么样,但实际上真正进洞房过日子了,才知道这人到底咋样。
我和卢导(卢伦常)认识大概十几年了,在《对手》之前就合作过,相互非常了解,比如她很了解我写这场戏的目的是什么,重点在场景、在台词、还是在人物关系的变化,她都知道。我也很了解她,如果遇到场景解决不了的情况,需要改剧本,她也不会把我剧本里真正重要的部分改掉。所以这种默契,确实需要时间、需要多次合作去培养的。
当然,我也憧憬和一些没合作过的优秀导演合作,但我目前更倾向于知根知底的合作对象。因为对编剧来说,确实容易出现一种情况:你花很多心血的剧本,交到一个导演手上,最后成片出来,发现是另一个故事。这次《黄雀》的创作,不管是导演、制作、演员表演,肯定都是对剧本加分的,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
澎湃新闻:这次还是和郭京飞合作,聊聊感受?
王小枪:我们之前也是有一个口头约定,就这个剧会找他来演,所以写的时候,你大概也有个人物的样子,可能创作中启发更多。郭京飞老师确实有很多幽默的小细节。越是这种剧情密度高的泛悬疑剧,或者说犯罪类型片,可以有一些幽默来点缀一下,就不会那么沉重。
而且人物为什么叫郭鹏飞,我们剧名叫《黄雀》,大鹏是一种很大的鸟,每个人年轻时心中都有一只大鹏,觉得自己未来肯定很牛对吧?对于郭鹏飞来说,他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,走路姿势都虎虎生风,但经历了生活的毒打和命运的耳刮子抽来打去,最后发现自己就是小小的一只麻雀。郭京飞把这个角色年轻时的那种意气风发,和中年后的有点中年危机,窝囊有点颓的状态演得非常好,让我印象很深。

郭京飞 饰 郭鹏飞
澎湃新闻:谈到中年危机,《对手》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在一个谍战故事里,嵌套了一对夫妻的中年危机叙事。这次《黄雀》你提到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走向中年危机的颓唐。这是你近几年创作中比较想表达的母题吗?
王小枪:这个故事有比较大的时间跨度,从1980年代、1990年代,到2004年。我自己的感觉吧,我们这一代人回顾过去的几十年,可能会有一种活了两世的感觉。
我是1979年生人,我小时候的社会环境、治安、经济、观念各方面,跟现在相比,像是另一个世界。那么郭鹏飞这个角色,在这样迅速变化的时代浪潮冲击下,他从生活和精神上一定会受到很大冲击,一定会给他带来一些中年危机的东西。
当然,我的年龄可能也快到中年危机了,所以我也有一些感同身受的东西会不自觉地放进去。我们作为编剧,要给观众提供的不仅仅是情节的堆砌,肯定要植入一些情感上的共鸣,或者一些五味杂陈的东西。
剧本创作是“马拉松”,要沉住气
澎湃新闻:“长剧短剧化”是这几年编剧逃不开的魔咒,你怎么看待这五个字?
王小枪:现在我们经常在探讨,比如短视频对于长剧集的冲击,或者倍速看剧带来的一些创作趋势等等,好像大家要一味地快。但我个人认为,一味地短,不一定一味地好,它还是相对的。
相对于节奏是不是要越来越快,我首先认为肯定要保持创作里的卷,卷就是最好从人物上没有一个废角色,分场上没有一场废戏,台词上没有一句废话,所有创作的信息都是有效的。
还有种情况是我们应该注意的,观众为什么弃剧?为什么不喜欢看?为什么觉得慢?不是它的速度出了问题,而是要注意到观众对新内容、新题材的渴望,从人性角度讲,人肯定是喜新厌旧的。这个问题远大于所谓的节奏快慢。
作为编剧来讲,最好从创作最初就要能提供一种叙事的不同。比如公安题材,好多都在写扫黑写命案写连环杀人,那咱们能不能另辟蹊径,找一些大家不太关注的警种去写?比如让我现在写一个《县委大院》的续集,我可能不写县长了,我能不能写门卫,这个门卫在县委单位干了一辈子,他会有怎样的故事和观察?
澎湃新闻:有没有近几年你比较喜欢的电视剧作品,你觉得它在“长剧短剧化”的尝试上,做得有点东西的?
王小枪:我举个例子,《繁花》。大家好像会天然地认为它是一个经典长剧代表,但实际你观察它,它的叙事节奏非常快,它的情节密度也非常高,制作还精良,是集合了非常多优点于一身的。大家一说强情节快节奏,容易觉得一定是悬疑剧才能做到,实际上不是。《繁花》不是典型的强情节,也不是悬疑剧,但它能做到快节奏,而且不是为了快而快。
澎湃新闻:很多时候,快节奏强情节容易牺牲人物和情感,但《繁花》做到了快节奏,也没有丢失人物,而且情感浓度还非常高。
王小枪:对,所以我觉得一个剧的好,一定是全方位的。很简单,木桶理论,没有哪个剧单独一个长板特别长就能令它成为经典好剧的。
澎湃新闻:前面我们谈到“活了两世”的感觉,我们不仅会观察到自我的变化,时代的变化,作为影视从业者,你也见证了行业二十年的变化。能否谈谈?
王小枪:作为编剧,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确实会遇到不同的行业信号,比如说某段时间,有些题材过时了,有些类型不让写了。前些年最明显的信号是IP热。所有人来都聊IP,我说我想写原创,可能有的朋友就劝我,别做原创,太累了还出不来,就做IP改编。现在长剧短剧化,可能又是另一种信号了。
我觉得,当然要面对和拥抱外部环境的变化,但总体来说,万变不离其宗。其实现在来看十几二十年前的一些作品,放在当下看,还是能让你心生感慨,让你五味杂陈,让你振奋或者忧伤。它们能够穿越时光,核心还是生动的人物,精彩的情节,优秀的表演所有这些的综合。
总体上,我觉得编剧还是应该沉住气,本来剧本创作就是马拉松,你跑马拉松,旁边观众怎么加油,你也得悠着劲跑,你发疯一样跑,跑两步就没劲了。还是要理性看待吧。好的作品就是需要时间,光着急没用。
澎湃新闻:展望未来行业的发展,你觉得有哪些新趋势和方向是值得编剧去关注的?
王小枪:原来行业里总体会觉得,一个项目做得足够好,它能男女老少通吃,比如像《狂飙》这样的戏。这种情况我觉得未来出现的几率会降低。
将来可能咱们写什么剧,就要清楚地定位到我们服务的是怎样的观众群体,不能又要年轻女性观众,还要银发经济;既要高知群体,又要足够下沉,这不太可能。大家的选择就是越来越垂直细分了。另外就是,可能季播会成为趋势。
澎湃新闻:你是医学专业出身,进入编剧行业。如何靠自己的学习来成为优秀的编剧?
王小枪: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写、多生活。当然,这两句话我说起来好像挺虚的,但确实是这样。
“多写”是因为所有写作经验和技巧的积累,只能通过多写。就像做手术一样,你做1万台手术,我做100台手术,我天赋再高,我也比不过你的。因为没有遇到过1万台手术里的那么多问题,我无法积累那么多经验。
“多生活”,我们现在有的戏的悬浮,是因为编剧在剧作层面上没有往人物内心更深一步走。比如我写一个法官,我觉得法官就那样严肃,你都不去法院看看吗?写一个反扒民警,你不去跟着抓一次小偷?很多东西无法通过想象完成。
澎湃新闻:你人生中有几次大的行业转向,比如从医生到作家,从编辑再到编剧。如果人生将来再发生一次职业转向的话,会比较期待做什么?
王小枪:我不希望再发生变化了,觉得现在挺好。我已经很幸运地找到了职业和兴趣的结合,我可能已经找到了我此生最喜欢的工作。
上一篇:指南针股票软件最新价格表
下一篇:指南针原始股票收益分析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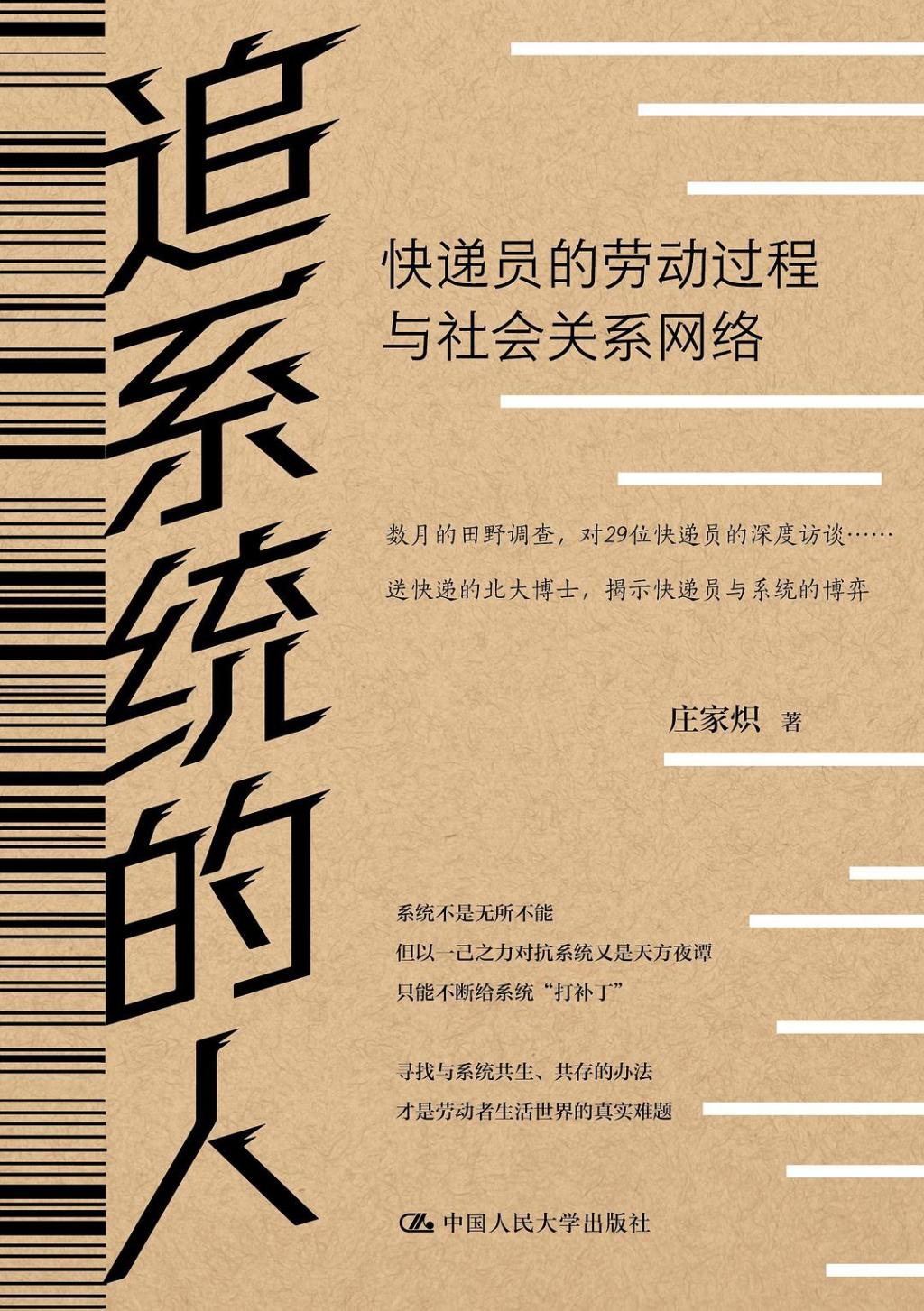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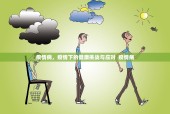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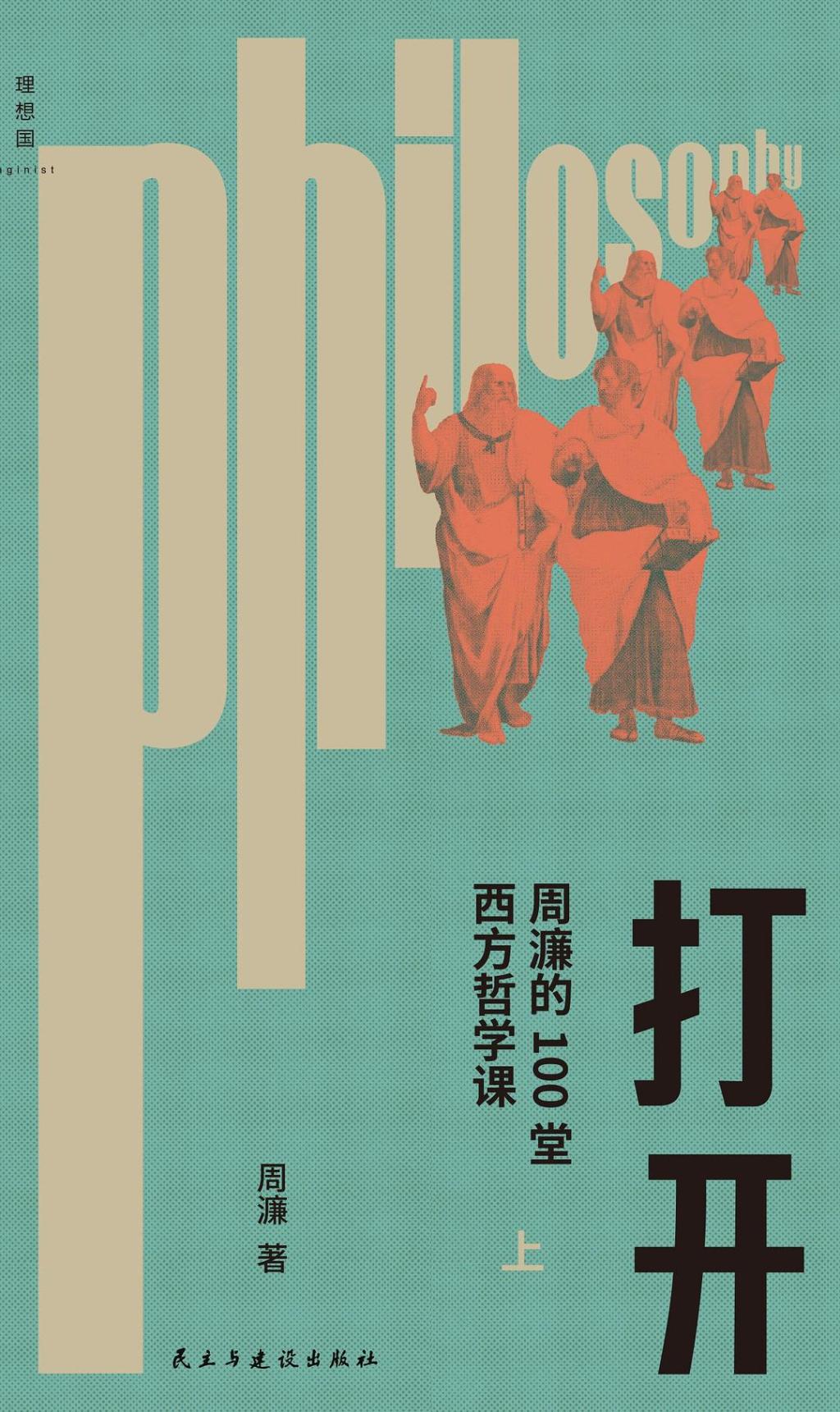
有话要说...